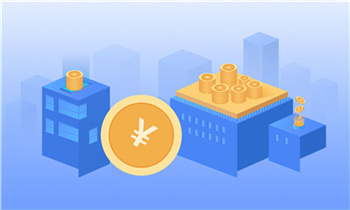在我的生活中,没有什么称得上重要的事。我习惯把双腿丢在衣柜里,躺在床上,和床头的猫聊天。
猫的身体从床头靠背和墙壁的缝隙中伸出来,像是鬼魂一样。猫说她就是鬼魂,这张床刚刚被安放在房间里时,她正在角落里晒影子,突然,我把床往墙壁一推,床安好了,猫也出不来了。
开始的时候,猫还会三天两头地请求我,她说她的血肉已经腐烂,希望我能把床板挪开,取出她的白骨安葬。可是我懒得去,床上挺舒服的,这一趟也许用不了几分钟,但下一次回到床上时,我的心态就变了,我便不是原来的我了。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猫渐渐习惯待在我的床头,我从不下床,床便一直是温暖的。等到我心情好些时,偶尔也会撸撸猫的头,理顺她棕橘相间的毛发。猫也会理我的头发,我从不下床,自然也没机会理发,头发越积越多,堆得床下到处都是,猫的爪子够不到床下的部分。听猫说,似乎有老鼠在我的头发里挖洞做窝。
猫和我的相处时间也不短了,谈话间,她总是提到她的尾巴。她的尾巴和她一样温顺,会在她高兴的时候微微摇摆,在她生气的时候狠狠翘起。猫很想念她的尾巴,尾巴没有她这么好运,被压在床底时连头都探不出来。有时,猫会想她的尾巴想到哭泣,发出凄惨的呜呜声。这时,床底的尾巴也会敲打着床板作为回应。他们这一唱一和动辄响彻整个夜晚,搅得我觉都睡不安宁,不得不用被子把头盖起来,才能勉强入睡。
猫总是怀念从前的日子,那时的她可以轻松地跳上房檐,钻进塑料管道,或是爬上树抓抓麻雀,再不济,摇着尾巴去找路人要点火腿肠,这些事都很令猫开心。可那时,她却只想着趴在影子底下睡觉,任凭尾巴怎么搅动,也不想睁开眼睛。猫真的很后悔,现在的她,哪也去不了了。我也为猫感到惋惜,如果她能动的话,说不定还能帮我取取快递,应付一下那些敲门的邻居。
猫说着又开始哭泣,我不太理解猫的心情。外面的景色也许千变万化,但也不过几棵树,几堆土,几座坑罢了,看来看去都那样。不如躺在床上看看手机,我想做的每一件事,都有人帮我做好了,我只用隔着屏幕动动手指,看着就好。猫也不理解我,她不爱喜欢手机刺激的光线,对她来说,那是有害的,会弄瞎她的眼睛。时间长了,猫也时不时看看我的眼睛,嘀嘀咕咕的,好像是在考虑我瞎掉以后的事情。
也许猫说的对,渐渐地,我开始越来越消瘦,开始对光线和寒冷变得敏感。窗帘是开着的,所以我只能白天睡觉,晚上再醒来。有时我会害怕,我这一生,本该成为骑士,成为诗人,成为受人敬仰的歌唱家。但现在,我被困在了这里。假如我贸然起床(那几乎要耗尽我全部的力气),猫必然会得寸进尺,要求我从床下勾出她的白骨;要求我剪掉那些头发,赶走那些老鼠——那本该是她自己要做的事,不是吗?
想到这里,我愈发坚定了躺在床上的信念,像我这样的人,根本不可能成为成为骑士,诗人,歌唱家。现在回头已经太晚了,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我,我为何不遵从自己的内心,仅仅是过好自己的一生呢?
突然,卧室的门被一群陌生人粗暴地踢开。我从没见过那群人,他们也像没看到我似的,将一张巨大的床塞进了我的卧室,压到了我的身上。我那脆弱的床板应声粉碎,折断的木屑刺进了我的皮肤,我被压在了那沉重的床底下,很快没了呼吸。
他们打开衣柜,把我的双腿像垃圾一样丢到窗外,然后放了一双崭新的腿进去。其他人离去后,床上又只剩下一个人,只不过这次,那个人不再是我。
猫终于和她的尾巴团聚,它们抱在一起,碎成几块,发出吱吱的声音钻到墙角的洞里去。
无聊随便写的,这算意识流吗?不知道,我没研究过意识流,无所谓了  ̄ω ̄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