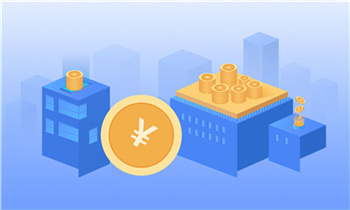“三代”一词,最早见于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”,是指夏、商、西周,秦以后也开始包括东周,并且一直沿用下来。“三代”所创造的高度文化成就受到了处于思想交锋中先秦诸子的追捧。回望“三代”,是中华思想文化向后看思维定式的显著标识之一,由此也形成了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独具民族文化特质的“三代”情结,这一特质在齐梁时期的刘勰身上体现得极为鲜明。《文心雕龙》中“三代”一词,出现七次,夏、商、周出现的次数更多,至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等三代圣王则是高频出现,作为“三代”文化载体的“六经”以及乐舞、乐器、乐歌、礼制、礼器等也被其一一拾掇进去,从而展现出一幅具有浓郁“三代”政教文化色彩的历史画面。在儒、释、道三家之学并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,刘勰的这一偏好,独树一帜,的确不同于这一时期那些伟大的批评家。刘勰的“三代”情结体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“郁郁乎文哉”的价值导向,一是“征圣立言”的神圣书写,一是“原始表末”的路径依赖。
“郁郁乎文哉”的价值导向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“郁郁乎文哉”的说法,源于孔子。孔子以传承宗周文明为己任,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为教义,“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”(《礼记·中庸》),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对“三代”文化一往情深,故而有“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”(《八佾》)的感慨。孔子以“三代”礼乐文化为“文”的思想对刘勰的影响很深。对“三代”文化成就,刘勰推崇备至,“斯文之兴,盛于三代”(《文心雕龙·铭箴》),“三代政暇,文翰颇疏”(《书记》),“三代所兴,询及刍荛”(《议对》);对周代更是不吝赞美之词,“周监二代,文理弥盛”(《章表》),“近褒周代,则郁哉可从”(《征圣》),“周世盛德,有铭诔之文”(《诔碑》)。他秉持以礼乐之文为“文”的正统理念,在“三代”礼乐文化的各种载体中探寻“文”的源头,致力于阐释各种文体皆源于“六经”。《原道》篇开宗明义,刘勰明确断定“文”乃“三才”之文、礼乐之文,天文、地文和人文以反映天经地义之至理而具有一致,以此作为全书弥纶群言、原始要终的基础。从天文到地文到人文的同一性推断可以看出,刘勰对商周以来天、地、人“三才”合一宇宙观、世界观的全面吸收与赓续发展。从《征圣》篇“政化贵文”“事迹贵文”“修身贵文”的语义所指来看,刘勰不仅将“文”的源头指向“三代”,而且宗周的色彩极为鲜明。纵观《文心雕龙》一书,“本乎道,师乎圣,体乎经,酌乎纬,变乎骚”(《序志》)的总体原则,均是在三代“尚文”观念的笼罩下,在“郁郁乎文哉”的价值导向中形成的。
“征圣立言”的神圣书写
“征圣立言”思想,源于“轴心期”诸子。晚周以来,五霸七雄纷争,社会激烈变迁,诸子欲拨乱反正,但人微言轻,遂借托古构想,借尧、舜、汤、武打压霸主,灌输王道理想。在思想谱系与文化心态上,诸子塑造了上古帝王的伟大人格与传承谱系。孔子对此不遗余力,墨子道夏禹,孟子言必称尧舜,许行则为神农之言,庄子臆造古圣先王之说(罗根泽《晚周诸子反古考》),以此建构古史的“黄金时代”。这是“三代”情结产生的历史语境,也是中国历史上道统思想的历史依据。刘勰对前代圣王不乏溢美之辞,有着鲜明的圣王崇拜意识,视前代圣王言行举止为万世不变之遵循,诸如“玄圣创典”“素王述训”“文王患忧”“公旦多材”“夫子继圣”(《原道》)的赞誉;又诸如“帝轩刻舆”“大禹勒筍簴”“成汤盘盂”“武王户席”“周公慎言于金人”“仲尼革容于欹器”(《铭箴》)的褒扬。刘勰有着明确的“征圣立言”意图,所谓“征圣立言”就是为文学立法,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《文心雕龙》全书中有那么多的文学法则,譬如“体有六义”(《宗经》)、“八体”(《体性》)、“三准”(《镕裁》)、“四对”(《丽辞》)、“练字四要”(《练字》)、“二患”(神思)、“立文之道,其理有三”(《情采》)、“六观”(《知音》),等等。从《原道》开篇来看,刘勰宣称本书的写作目的,就在于传达“道”的神圣性、验证“圣”的合法性和效仿“经”的永恒性,他坚守荀子以来原道、征圣、宗经的立场,捍卫“三代”以来神圣书写的意图,可谓异常坚定。
“原始以表末”的路径依赖
“究始终”“探表末”是《文心雕龙》写作方法上的主要依凭,刘勰称之为“原始以表末”,也称之为“原始要终”。历史地看这一思想的源头,一是源于《周易》,并经由汉代司马迁的阐发;一是源于墨子的“三表法”,是对“有本”“有原”“有用”三条标准的阐发。在《史传》《章句》《附会》《时序》诸篇中,刘勰反复提及“原始要终”,并于终篇归纳为“原始以表末,释名以章义,选文以定篇,敷理以举统”(《序志》)四种写作方法,可谓心心念念、不厌其烦。刘勰长于“原始以表末”的研究方法,《文心雕龙》各篇均以此方法来论述文学问题。譬如《明诗》篇,刘勰以“铺观列代”“撮举同异”为原则,将诗歌之“始”上溯到葛天氏之乐,历述黄帝、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时期的代表作品,在此基础上叙述汉代以后四言诗、五言诗的演化历程。他秉承“究始终”“探表末”的法则,当一个问题不得解时,将其“始”追溯到“三代”,便会进入正统的谱系,获得不证自明的合法性,这是包括刘勰在内的古代学者的常见写法,在古籍中屡屡可见,是古典时代的传统,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。见于《文心雕龙》一书,如《辨骚》:“固知《楚辞》者,体慢于三代,而风雅于战国。”《诏策》:“命之为义,制性之本也。其在三代,事兼诰誓。”《养气》:“三代春秋,虽沿世弥缛,并适分胸臆,非牵课才外也。”《才略》:“九代之文,富矣盛矣;其辞令华采,可略而详也。”凡此种种,振叶寻根、观澜索源,“三代”情结的印记清晰可见。这种探究问题原委、始末,并将其追溯到“三代”的路数,是贯穿《文心雕龙》全书的重要书写路径,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刘勰在写作方法上的路径依赖。
刘勰虽然深知“时运交移”“与世推移”(《时序》)的道理,也明了“三代玉瑞,汉世金竹,末代从省,易以书翰矣”(《书记》),遵循着从省从简的趋势,但在其有意的建构、刻意的修饰甚或不经意的陈述中,或多或少地都流露出对“三代”的仰慕之情。回望“三代”是中华思想史上一个常见的主题,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导向、书写方式与方法路径。就此而言,刘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
(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 夏静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